[文章编号]1001-5558(2019)01-0108-11

●齐木德道尔吉 高建国
摘要:在蒙古国新发现的《封燕然山铭》摩崖是东汉窦宪北征匈奴后的纪念性遗存,与《后汉书》所记存在多处细微差异,个别异文可与蒙古国考古资料印证,凸显摩崖仍具有重要的文献研究价值。结合史籍记载和蒙古高原地理可知,传世文献中的燕然山确为今蒙古国的杭爱山,摩崖所在是中原与漠北之间的一处重要交通点。摩崖下方的“汉山”题刻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再综合前述多处差异,推测班固后来对文本进行了润饰。
关键词:蒙古国;杭爱山;燕然山;班固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86/j.cnki.62-1035/d.20190131.008
2017年7月27日至8月1日,应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校长喇呼苏荣博士的邀请,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携同延安大学高建国飞赴乌兰巴托,组成中蒙联合调查队,对蒙古国中戈壁省德勒格尔杭爱县一处汉文摩崖进行实地考察。经现场认读、辨识、抄录和制作拓片,确认该摩崖为东汉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铭》,是永元元年(89年)汉朝与南匈奴、乌桓、西戎氐羌等部族结成联军深入北匈奴腹地、大败北单于后刻石颂功的纪念性遗存。《封燕然山铭》摩崖在蒙古国发现的消息甫一公布,引发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就《封燕然山铭》的历史背景、摩崖性质、文化意义等内容,一些学者已从不同层面作了详细解读[1]。有关摩崖考察经过、周边环境及摩崖内容,笔者已撰《蒙古国〈封燕然山铭〉摩崖调查记》一文做了报道[2]。现就该摩崖的文献价值、所处位置与杭爱山空间差异,还有不为人知的“汉山”题刻三个问题,作一初步研究。
一、 《封燕然山铭》摩崖的文献价值
《封燕然山铭》摩崖刻于东汉永元元年(89年),是窦宪北征匈奴获胜后令班固所撰的铭文,意在“刻石勒功,纪汉威德”[3]。摩崖反映的是班固最初的文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笔者花费两天时间,现场对摩崖作了逐字逐句辨识,除去漫漶不清之处,共识读和记录了 229 字。摩崖为汉隶竖刻,从右至左共20行。石面经简单处理,凹凸不平。右侧起首部分石质多有碎裂,文字漫漶,无法辨认;中间及结尾部分保存稍好,多能辨识。限于自然条件及技术,所获拓片质量较差,深为遗憾。摩崖与《后汉书》所记存在多处细微差异。为便于比勘,再将考察辨识结果移录如下。异文处理用[/],斜杠前为《后汉书》所用字,斜杠后为摩崖用字;方框[]内的字,表示摩崖无法辨识、据其所处位置与《后汉书》对比后可以确认的字;字下划线者,表示《后汉书》有、摩崖无的文字;括弧内的阿拉伯数字为摩崖行数。

(1)惟永元元年[秋七月],
(2)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
(3)[登翼王室], [納於大麓],維清緝熙。[乃/迺]與執金吾
(4)[耿秉],述[職]巡[御/圉], [理]兵[於/于]朔方。[鷹揚]之校,
(5)[螭虎之士], [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
(6)[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三萬。
(7)元戎[輕]武, [長轂]四分, [雲/雷]輜蔽路,萬有三
(8)千餘乘。[勒]以八陣, [莅/蒞]以威神,玄甲[耀/燿]日,
(9)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
(10)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
(11)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 [蕭/條][條/平]萬里,野
(12)[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落],反斾而[旋/還],考傳
(13)驗圖,窮[覽其]山川。遂逾涿邪, [跨/進]安侯,乘燕
(14)然, [躡/汙]冒頓之[區/逗][落/略],焚老上之龍庭。上
(15)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
(16)安固後嗣,恢拓[境/彊][宇/寓], [振/震]大漢之天聲。茲
(17)所謂[一/壹]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
(18)[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 ]① 辭曰:
(19)[鑠]王師兮征荒裔, [剿/癹][凶/匈]虐兮[ /釓]海外。夐[其邈]兮
(20)[亙地界],封神丘兮建[隆/陸][嵑/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后汉书》所记《封燕然山铭》全文 295 字。摩崖现存可辨识文字有 229 字,占《后汉书》所记录的四分之三强。摩崖中无、《后汉书》有的文字有 10 个,分别是:第 2 行的“漢”,第 3 行的“緝熙”,第 13 行的“遂”,第 17 行的“乃”,第 19、20 行的 5 个“兮”字。摩崖与《后汉书》所记明显不同的文字有 24 个,分别是第 3 行的“廼”,第 4 行的“圉”“于”,第 7 行的“雷”,第 8 行的“蒞”“燿”,第 11 行的“條平”,第 12 行的“落”“還”,第 13 行的“進”,第 14 行的“汙”“逗略”,第 16 行的“彊寓”“震”,第 17 行的“壹”,第 18 行的“ ”,第 19 行的“癹”“匈”“釓”,第 20 行的“陆”“碣”。
这些存在细微差异的文字有异体字,有同音字。个别文字与《后汉书》所记颇有区别,极具文献价值。如第 14 行的“汙冒頓之逗略”,《后汉书》作“躡冒顿之區落”,“汙”字被“躡”字取代,“逗略”被“區落”顶替,使得该句所含内容与摩崖所记大相径庭。“逗略”,应与“逗落”同音,当是匈奴语“墓冢”之意。《史记》载:“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裴骃《史记集解》引晋张华语注:“张华曰:匈奴名冢曰‘逗落’。”[4]杜佑《通典》移录此节,在相同位置注文为:“晋张华曰:‘匈奴名冢曰豆落’。”[5]与“逗略”对应的是“龙庭”。龙庭应即龙城,“庭”谓单于庭。《后汉书》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6]因此,龙城既是匈奴人聚会祭祀、娱乐之地,也是单于处理政务之所在。“汙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这是一句对仗工整的互文句式,其意为汉匈联军获胜之余,污染了冒顿单于坟墓,焚烧了老上单于的龙庭。毁坏敌人坟墓与宫城,是原始部落时代遗留的陋习。考古资料显示,陶寺遗址就存在这种迹象[7]。
汉匈联军能搜寻到单于坟墓吗?答案是可能的。首先,蒙古国的考古发现显示,在匈奴龙城以西的鄂尔浑河谷地带发掘到多座匈奴贵族墓葬,如高勒茂都1号、2号墓葬,出土器物和墓葬规格均显示其为单于级别的墓葬——而这里正是汉匈联军出击的军事目标。其次,汉匈联军中有随军出征的乌桓人,早在西汉昭帝时期,乌桓人“乃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单于之怨”[8]。汉匈联军要想发现单于墓并不困难。
《后汉书》所记“區落”一词,仅是一个普通的汉语词,含义较为宽泛,后人注解为:“区落谓(冒顿)东灭东胡,西走月氏,南取楼烦,悉收秦所夺匈奴地。”[9]显然,该注释认为“區落”为冒顿单于的领土与部落。摩崖明白无误地记录了污损冒顿单于墓冢,这与《后汉书》所记蹂躏践踏冒顿单于之领地部落完全不同,却与蒙古国考古资料高度吻合。
据蒙古国北杭爱省温都尔乌兰县哈内河谷巴拉嘎孙塔拉高勒茂都 2 号匈奴墓葬群发掘报告,其中的 1 号贵族墓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盗劫。该发掘报告称,1 号贵族墓墓道长 37m,墓室东石壁长 48m、高 3.5m,北石壁长 46m、高 4m,西石壁长 48m、高 2~2.20m。南面石壁除去墓道有 42m 长,墓道宽约 8m。其椁用圆木筑成,棺用木板,外镶金边。由于破坏和盗劫严重,无法复原棺内情形。墓葬顶部石头覆盖层的正中,有直径 12~13m、深 2~3m 的圆形坑洞,疑为古时盗墓者所为。最上层到下面 16m 处为止,用一层石头、一层沙子的构造方式覆盖主墓室。墓室石壁外面 5m×8m 的隔间葬有 20 多匹马和 5~6 只羊的骨殖。另一室中埋葬着一辆带有轿伞的木质舆车,左侧车轮及相关部件不存,据此侧显现的盗洞推测,极有可能是被盗所致。16m 处往下是 60cm~120cm 厚的木炭层,炭层呈洼陷状态,其下再一层石头,然后就是圆木椁室。椁室隔成三部分,最西面为器物,东面的是舆车配件,中间为棺室。棺室上方形成四方形盗洞。棺材仅剩东侧下面的三块木板,外面包有黄金镶饰。骨殖不存,仅存一面 23cm直径的玉璧。陪葬物未被盗扰,仅主墓室和骨殖被破坏,此种现象反映这不是简单获取财宝的盗墓行为,应是有意的破坏行为。此外,墓地正北十多米处有东西向排列的 4 排 13 对石头组成的祭祀场地,其周围散布着 30 座中型和小型卫星墓葬,1 座殉马葬场。而这些墓葬无一例外,全部被盗过。考古资料显示,这是一座巨型匈奴贵族墓葬,其规模和级别以及陪葬物的丰富程度远超学界熟悉的诺颜乌拉匈奴贵族墓[10]。除此之外,诺颜乌拉 12 座匈奴墓葬,北杭爱省高勒茂都 1 号匈奴墓地 3 座大型墓葬及 18 座小型墓葬,高勒茂都 2 号匈奴墓地 2 座墓葬,肯特省巴彦阿达尔嘎苏木 4 座匈奴墓葬,科布多省芒汗苏木 3 座匈奴贵族墓葬,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查尔曼 6 座匈奴贵族墓葬,苏吉地方的 1 座墓葬,经过发掘,确认全部遭受不同程度的盗扰和破坏[11]。
蒙古国考古资料显示,汉匈联军获胜后的泄愤行为当属可能。这种近似宗教亵渎的行为当是表达了一种深层的政治含义:向上天宣告,汉军已经完全捣毁了匈奴帝国,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和政治成功。因此,摩崖中的“逗略”一词,不仅是一个珍贵的匈奴语词,且其所表达的含义更接近于班固书写铭文时的历史现实,而“區落”一词却不具备以上两种价值的任何一种。
再如,摩崖“條平萬里”“域滅區落”“反斾而還”“遂踰涿邪”“進安侯”“恢拓彊寓”“震大漢之天聲”“癹匈虐釓海外”等句,《后汉书》记录分别为“蕭條萬里”“域滅區單”“反斾而旋”“踰涿邪”“跨安侯”“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剿凶虐兮 海外”,个中字词差别虽小,表示的意义却不尽相同。从《文选》开始流传的《封燕然山铭》,在《后汉书》的基础上又稍有差异,如“域滅區單”“昭銘上德”,《文选》记为“域滅區殚”“昭銘盛德”。窦宪等人举行的封山之礼原为祭天,摩崖所言“昭銘上德”当即此意,而“盛德”则失去了祭天的意义。
还有,第1行“秋七月”三字,摩崖在相应位置几乎没有任何刻画的痕迹。第2行“寅亮”两字本处行尾,但在相应位置也没有任何字迹,与其他行末相比,明显存在两个字的空位。第18行的“其”字、第20 行的“碣”字,均为异体字。第 19 行的“釓”字同“釚”,仅见于居延汉简。
《封燕然山铭》摩崖与《后汉书》存在的多处细微差异显示,摩崖依然具备极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特别是“汙冒顿之逗略”一句,可与蒙古国匈奴墓葬考古资料相印证,透露出汉匈联军获胜后的一些重要行为。这种泄愤行为,在班固所作的《窦车骑北征颂》一文中被表达为“揣城拔邑”[12];而经润饰流传的《封燕然山铭》,却修改为“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犹表示胜利之意,却掩盖了原始文本的重要信息。
二、 《封燕然山铭》摩崖与“燕然山”
《封燕然山铭》摩崖的发现,对于考订燕然山的位置及汉代蒙古高原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地理坐标意义。以常理论,摩崖所在即为燕然山,然而,国内学界所认识的燕然山是今蒙古国的杭爱山。杭爱山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西南,核心地域包括今前杭爱省、后杭爱省和扎布汗省辖地,西北东南走向,是一座绵延 700 公里的巨大山脉,但摩崖所在山丘仅在杭爱山余脉,距杭爱山核心区域尚有一定距离,则此山丘是否仍可称作“燕然山”① ?将燕然山认定为杭爱山,是否有文献佐证?
《中国历史地图集》按照历代对蒙古高原地理情况的记述,将杭爱山在汉代标为燕然山,在隋唐时标为于都斤山、乌德鞬山,在蒙元时标为杭海岭,至清代才标为杭爱山。如此标注,可能与清代以来的文献记述有关。《嘉庆重修一统志》直指杭爱山“此当即古之燕然山”[13]。相比其他王朝,清人对蒙古高原历史地理有了较多了解,但直指杭爱山为燕然山仅为推论之言。
两千多年来,匈奴、鲜卑、乌桓、柔然、突厥、契丹、回纥、蒙古等多个民族先后活跃在蒙古高原上,高原地貌相对稳定,但民族变迁引发的语言面貌却时刻在改变着,而不同时期的汉语也在发生变化。各种原因导致了杭爱山在不同时期名称不一。要想直接将杭爱山对应为燕然山,难度较大,但通过探索燕然山名的最早出处,及摩崖西向翁金河、推河、拜达里格河与汉匈战争、北魏与柔然战争的关系,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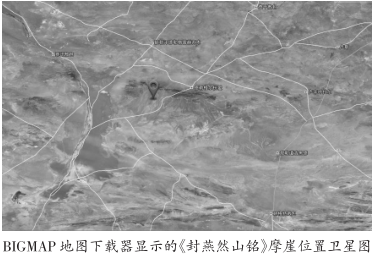
摩崖西约 30 公里处为翁金河,源于杭爱山南麓,自北而南长约 500 公里,最终流入茫茫戈壁。翁金河(Onggi/Onggin),是元、清代以来的称谓,元代的汉译为“汪吉河”,读音与 Onggi无异,而西汉时的称谓为“蒲奴水”,北魏时称为“栗水”。推河与拜达里格河更在翁金河西,前者汉代称为“姑且水”,北魏时称为“兔园水”;后者汉时称为“匈奴河”,清代以来称为“拜达里格河”。两者均是杭爱山南麓的重要河流。
汉朝因为在立国初期有过“白登之围”的惨痛教训,因此一直采用和亲的办法羁縻匈奴。汉武帝即位后,和亲断绝,汉匈关系骤然紧张。汉军主动出塞击匈奴,始于元朔五年(前 124年)。史载汉军由大将军卫青率领,出朔方、高阙塞,“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此时单于王庭还在漠南,汉军出塞不远即遭遇匈奴兵。此后一年,卫青再次从定襄出塞,投降匈奴的汉军将领赵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从此,汉军要想出塞攻击匈奴,必须长途跋涉,“绝幕”之后才能击杀敌军。元狩四年(前 119 年)漠北之战,卫青、霍去病分率两支大军,“咸约绝幕击匈奴”,分别从定襄和代郡出塞,最终深入漠北,重创匈奴各部。其中,卫青率领的西路军,最终抵达阗颜山赵信城;霍去病的东路军则直抵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阗颜山赵信城的确切地址仍不确定,依行军路线分析,卫青出塞,当经翁金河以东、以北地域。
漠北一战,匈奴遭受重创,依汉军后期出塞路线看,匈奴人明显有西迁的迹象。如元鼎六年(前 111 年),公孙贺出九原“二千余里”,赵破奴从令居出塞“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均“不见匈奴一人”。依《中国历史地图集》,匈河水即今蒙古国的拜达里格河。
匈奴向西北方向退却,汉军此后的出塞目标便转向翁金河西南地区。如太初二年(前103 年),赵破奴再“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浚稽山的地望很清楚,位于今戈壁阿勒泰山,在翁金河西南方向。天汉二年(前 99 年),汉军再次出击匈奴,目标直指涿邪山、天山方向,地望更在浚稽山以西。
因此,在武帝朝前述战役中,除漠北之战卫青出塞可能距离翁金河东不远之外,其他战役均在翁金河流域之外。但是,征和三年(前 90 年)李广利兵败被俘的战争,不仅第一次涉及“燕然山”,而且其行军路线恰在翁金河流域范围之内:
贰师将军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会贰师妻子坐巫蛊收,闻之忧惧。其掾胡亚夫亦避罪从军,说贰师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还不称意,适与狱会,郅居以北可复得见乎?”贰师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虏已去,贰师遣护军将二万骑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贤王左大将,将二万骑与汉军合战一日,汉军杀左大将,虏死伤甚众。军长史与决眭都尉煇渠侯谋曰:“将军怀异心,欲危众求功,恐必败。”谋共执贰师。贰师闻之,斩长史,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相杀伤甚众。夜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军大乱败,贰师降。单于素知其汉大将贵臣,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14]。

李广利此次北伐从五原出塞,目标直指浚稽山、涿邪山。汉匈遭遇的“夫羊句山狭”“范夫人城”正在翁金河正南方向不远之处。此时,李广利接到凶讯,妻儿因卷入丞相刘屈氂巫蛊案被下狱。李广利临阵决计逾越杭爱山,至郅居水(今色楞格河)寻找匈奴主力决战,设想以巨大军功保全性命。汉军要想快速进军,直抵郅居水,沿途需有水源保证,沿蒲奴水(即今翁金河)一路北上,翻越杭爱山东南麓山坡,再沿安侯河(今鄂尔浑河)而下抵达郅居水,这是理想路线。且此次战役中,另一路由御史大夫商丘成率领的三万余人从西河出塞,“军至追邪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15]“追邪径”当为“涿邪径”,商丘成军从涿邪径退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可见,匈奴人也是沿着蒲奴水(即今翁金河)退回杭爱山以北的,而从正南方向追踪而至的李广利军,也应是循着蒲奴水快速北上抵达郅居水南岸区域的。
这次战役,李广利孤军深入,且因部下产生离叛之心而不得不快速南撤。以常理言,李广利南撤还应循来时路线。“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遭遇匈奴单于五万兵力合围,李广利战败投降。“速邪乌燕然山”,语意、地理均不详,唐人颜师古解“速邪乌”为地名,解“燕然山”为山名[16]。值得注意的是,颜师古的注解是在东汉以来燕然山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山名的基础上作出的,《资治通鉴》将此山直接记为“燕然山”[17]。速邪乌到底是不是地名,其与燕然山到底是怎样一种构词,意义又如何,难以确知。笔者分析,史书中第一次出现燕然山的地方,应该也在李广利北上和南撤的路线上,即“速邪乌燕然山”应该在蒲奴水流域以北地区,而蒲奴水以北正是杭爱山东南。
南北朝时期的文献更证实了今杭爱山就是燕然山。北魏时期,拓跋鲜卑曾多次出塞征讨漠北的柔然人。《魏书》载,始光二年(425年)四月,太武帝拓跋焘亲征柔然:
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辎重轻袭之,至栗水,大檀众西奔。弟匹黎先典东落,将赴大檀,遇翰军,翰纵骑击之,杀其大人数百。大檀闻之震怖,将其族党,焚烧庐舍,绝迹西走,莫知所至。于是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世祖缘栗水西行,过汉将窦宪故垒。六月,车驾次于兔园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渡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18]。
太武帝此次亲征,绝幕之后抵达栗水、兔园水,即今蒙古国翁金河、推河。获胜之后,魏军四处寻找柔然残部,曾“北渡燕然山”。以前述两河地理较之于今日蒙古高原地理,此燕然山正为今杭爱山。日本学者谓燕然山“似为肯特山”,仅为推测,并无实据[19]。
《南齐书》《梁书》也记载到了燕然山,同样证实了燕然山即今杭爱山。《南齐书》载:“升明二年(478年),太祖(萧道成)辅政,遣骁骑将军王洪轨使芮芮,克期共伐魏虏。建元元年(479年)八月,芮芮主发三十万骑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虏拒守不敢战,芮芮主于燕然山下纵猎而归。”[20]刘宋联合柔然攻击北魏的这次战争,《梁书》也有记载:“宋升明中(478年),遣王洪轨使焉,引之共伐魏。齐建元元年(479年),洪轨始至其国,国王率三十万骑,出燕然山东南三千余里,魏人闭关不敢战。”[21]然据《魏书》载,柔然此次出兵显然没有引发大规模战争,“蠕蠕率骑十余万南寇,至塞而还”[22]。因此,《茹茹传》甚至没有提及此次战事。经过北魏多次打击,柔然人迁居到了燕然山北的地区,孝文帝时双方基本保持着和平关系。在刘宋使者王洪轨的怂恿下,柔然人翻越燕然山,企图再次南下。但世事突变,萧道成篡夺了刘宋皇权,并没有再次遣使柔然,更没有大规模出兵北伐,配合柔然行动。这可能是柔然人此次南下无功而返的主要原因。综合而论,《南齐书》《梁书》再次提到燕然山,且谓出燕然山东南三千余里可至北魏边塞,这与太武帝亲征柔然时“去平城三千七百里”抵达兔园水的道里是吻合的—— 其中七百里的差距,当是北魏边塞至平城的距离—— 而兔园水(今蒙古国推河)北的这座大山,正是杭爱山。
《中国历史地图集》将燕然山认定为今蒙古国杭爱山是可信的。“燕然山”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汉,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战败投降之地。北魏太武帝亲征柔然,抵达了燕然山南最重要的两条大河即栗水和兔园水,所记距离与《梁书》所载孝文帝时柔然南下魏塞的距离是吻合的。杭爱山是一座巨大山脉,西北东南绵延 700 公里,翁金河东岸的德勒格尔杭爱(Inil Hairan)山即是其绵延余脉。《封燕然山铭》摩崖刻在此处而不刻于杭爱山腹地,应从汉匈联军行军路线理解—— 沿翁金河北上,避开杭爱山腹地而仅穿越其东南山坡,再沿鄂尔浑河谷顺流而下,是汉匈联军行军最便捷的路线。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西路军统帅费扬古所率大军从宁夏和归化城出发,翻越大漠后在翁金河会师,由此北上直抵图拉河,再溯图拉河至昭莫多之地大败噶尔丹大军,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摩崖周边为辽阔草原,以此山丘为营地,可进可退。反之,恐怕没有哪支军队愿意翻越巍峨的杭爱山再去攻击山北的强敌。
三、不为人知的“漢山”题刻
在蒙古国此次新发现的《封燕然山铭》摩崖之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汉文题刻。该题刻位于摩崖下方距离地面不足两米处,字迹边框约半米见方,呈不规则四方形。题刻靠左,自上而下镌有 15cm 见方的两个大字,仔细辨识为“漢山”两字。其中“山”字镌刻痕迹明显,字迹清晰;“漢”字局部为黑色岩锈所覆,仔细辨认仍可识读。如按“漢山”两字大小估算,此处石面可镌刻四至六个大字,但右边石面大部分向内深度凹陷,且在“漢”字右边原本应该有字的部分明显有镌刻痕迹,然下部凹陷无痕。因此,笔者推测这处石面似是上部铭文题首的下移,原本应有两行或三行,由于镌刻时石面碎裂,只好在石面偏左部分仅镌刻“漢山”两字。与上部摩崖铭文相比,“漢山”两字字体较大,笔画稳健,字意古朴,隶意浓重。

摩崖石壁曾经过平整处理,而且在摩崖上方有明显经过处理的碑额状的斜面,似乎为镌刻题首而设,却未刻一字。细察崖壁,此斜面石质很差,并不具备镌刻题首的理想条件。“漢山”题刻是否为上部摩崖题首?其与摩崖是同时镌刻,还是比之早,抑或比之晚呢?依字体和逻辑而论,笔者以为二者当为同时镌刻。
汉代文献中保留的蒙古高原山川地名,多为匈奴语,如“涿邪山”“峻稽山”“燕然山”“狼居胥山”“姑衍山”“蒲奴水” “安侯河”“郅居水”“甘微河”“私渠比鞮海”等等。“安侯”,上古汉音*an*奕o,中古汉音*an*奕藜u,无疑是今“鄂尔浑”Orhon/Orqon 之更古时的读音。以汉字“安” (*an)记写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以后列高元音为首音,以-n,-l,-r 为尾音的音节,即 an~on,al~ol,ar~or,是完全可能的。 “侯”字(*奕o~*奕藜u),喉音为音节首音,圆唇央元音为音节尾音,记写*qon~*hon 音节,可得相对构拟结果*Orγo~*Orho。至于现在的 Orhon~Orqon 音,很可能是后代的传承中增加的名词词缀。该词的发音现象提示,汉代匈奴腹地的山川地名应是用汉语音读的匈奴语言,即在窦宪等人到达之前,蒙古高原上的山川地名均以匈奴语命名。所以,当汉军取得空前军事胜利之际,在蒙古高原用汉语命名一座山丘,取名“漢山”,或直接将“燕然山”改为“漢山”,这与窦宪等人当时所要表达的情感—— “恢拓疆寓,震大漢之天聲”是符合的。
然“漢山”题刻是否为后人所题?所谓“后人”,当包括中原人和外国人。以两字汉隶书写论,无论是中原人还是外国人,当对汉隶有着精深研究方可仿刻。如果真有这两种人存在,则其必为《封燕然山铭》摩崖的第一位发现者。南宋时期有位名为刘球的学者,著有《隶韵》一书,其中收录了《燕然铭》54 个隶书字体,然而并没有交代《燕然铭》如何获得。以其所收与现摩崖字迹相比,显然存在差异,且刘球并不具备发现《封燕然山铭》摩崖的时空条件。遗憾的是,除几处明显伪刻之外,古今中外的史籍中目前还没有任何宣称发现了《封燕然山铭》摩崖并在下部镌刻“漢山”二字者。因此,笔者认为,“漢山”二字与《封燕然山铭》摩崖是同时镌刻的,应是上部摩崖题首不得已而为的下移。即使如此,也未能镌刻完整。整体而论,这处摩崖应是在较短时间内刻的,并不具备理想的镌刻条件。
但随即而来的问题是,既然窦宪、班固等人给山取名“漢山”,并将其郑重其事地镌刻在石面上,那么为何此事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为何班固传世的作品是《封燕然山铭》而非《封汉山铭》呢?
梳理文献,结论令人意外。“封燕然山铭”作为班固此文的题目,始自南北朝的《昭明文选》。在此之前,并无文献以“封燕然山铭”为此文标题者。重新审视铭文,班固并没有明说此山即是燕然山。则“封燕然山”又是谁最早提出的呢?检索史料,其实还是来自班固作品。班固在回军中原以后,还作了一篇《窦车骑北征颂》的歌功颂德文章,其中“封燕然以隆高,广鞬以弘旷,铭灵陶以勒崇,钦皇袛以祐贶”之句最早提及“封燕然”一语[23]。与班固此文作于同时的崔骃《北征颂》一文,也使用了“勒功燕然,饮马安侯。藐瀚海,卑居胥”这样的表述[24]。崔骃也是宪府文学名士,“及出击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骃为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宪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骃高第,出为长岑长。骃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25]据此,崔骃也参加了此次出征,但他因切谏而不容于窦宪,可能半途就被打发离去。因此,崔骃颂文的信息应该来自班固等人的描述。这表明,班固回军后有意隐去了命名或改名及封禅“漢山”等事,并在歌颂窦宪的颂文中第一次使用了“封燕然”一语,他的同僚崔骃第一次使用了“勒功燕然”一语。后世文史学者不明就里,依着班固、崔骃的说法就将其命名为“封燕然山铭”。
《后汉书》记道,窦宪等人在胜利后“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以摩崖位置论,其距汉代朔方边塞似不足三千余里。据永元元年(89年)南单于屯屠何向汉朝的奏报,北单于“遯逃远去,依安侯河西”,因此“安侯河西”才是汉匈联军此次出兵的最终目标[26]。安侯河即今蒙古国鄂尔浑河,安侯河西即燕然山腹地及北麓,是历代匈奴单于聚会之所,也是多个草原民族政治活动的核心区域。从蒙古国学者在鄂尔浑河谷的考古发掘看,冒顿单于等历代匈奴单于墓葬及其生前活动的龙城,也位于此一区域。况且,按班固所言,窦宪等人确实抵达了安侯河畔并进行了一系列泄愤行为。《窦车骑北征颂》更详细地记录了汉匈联军的进军路线:“遂逾涿邪、跨祁连,籍庭蹈就,疆獦崝嵮,辚幽山、趋凶河,临安侯、轶焉居、舆虞衍,顾卫霍之遗迹,睋伊秩之所藐。”这再次明确地表明到达了安侯河西。如此,行军距离也才符合《后汉书》所记“去塞三千余里”的记录[27]。
窦宪率领的汉匈联军确实曾到达北匈奴腹地,并登临燕然山,但以摩崖现在的位置论,恐怕窦宪等人登临与刻石颂功并非在同一地点。铭文提及,汉军追击匈奴、俘获巨大之余,“逾涿邪、进安侯、乘燕然,汙冒顿之逗落,焚老上之龙庭”。仔细琢磨,此言是在追击战斗完成后、“反斾而还”,“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时所作,即前述进军路线是汉匈联军在回军途中查阅文献时所知。那么,汉军当时回军至哪里了呢?其实,班固此文已经给出了答案,“封神丘建隆碣”,即窦宪封山祭天、刻石颂功的山丘—— “漢山”。即窦宪等人在登临燕然山后率军南返,回至翁金河畔安营休整,并在摩崖所在山丘举行了隆重的封山祭天、刻石颂功等一系列庆祝活动。翁金河是连接漠南和漠北的重要交通路线,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窦宪等人在登临燕然山后返回翁金河畔休整,既有翁金河与周边草原提供水草等军需物资,又相对安全,进退无虞,在此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刻石勒铭,具备地理上的优越条件。此处也正是《魏书》所记的“世祖缘栗水西行,过汉将窦宪故垒”的地方。窦宪在此所建的军事设施336 年后还能保存下来,说明这里曾是汉军进军燕然山、跨安侯河的总支撑点。而摩崖所处山丘虽不在燕然山腹地,却仍然是其余脉,故而班固等人依然将其视为一山。所以在铭文中,班固“反斾而还”后并没有再次交代所处何山何地,仅称“封神丘建隆碣”。如此,窦宪等人封山祭天、刻石颂功与登临燕然山脉之间的空间差异就被忽略了。而班固在《窦车骑北征颂》中直书“于是封燕然以隆高”,崔骃也称“勒功燕然,饮马安侯”,更是让后人误以为窦宪所登临之山与刻石颂功之处是同一地点。此后文献如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均以此为据,袁宏直书“铭燕然山而还”[28],范晔也直书“镂石燕然”等语[29]。如此,既造成了千古之误,也使今人以为摩崖位置偏离了传统认识。
班固后来隐去命名“漢山”一事,或是有意为之。结合前述摩崖与《后汉书》二者文本间的差异,笔者推测,这种润饰很可能出于班固之手。《封燕然山铭》与《窦车骑北征颂》均笼统提及汉匈联军在漠北的破坏行动,而蒙古国高勒茂都匈奴大墓考古发掘所表现出的扰动似乎正好印证了“汙冒顿之逗落,焚老上之龙庭”的真实性。但这种泄愤行为,终不是文明社会认可的规则,故而班固于回军后即着手对铭文润饰修改,将最重要的“逗落”改为“區落”。至于为何要隐去命名和封禅“漢山”一事,也许崔骃《北征颂》中的一句颂词可提供点滴线索—— “师骋志兮元功克,封名岳兮表铭勒”[30]。封禅应在著名山岳举行,只有燕然山才能像狼居胥山一样代表匈奴名山,刚刚命名的“漢山”显然还不具备如此名气。四年后,随着汉和帝将窦宪集团突然铲除这样戏剧性的政治变迁,窦宪、班固等曾征讨北匈奴的人物,或下狱致死,或急于撇清与窦宪集团的干系,最终使得燕然勒石这段故事很快湮没无闻。袁宏《后汉纪》是除班固之外最早记述窦宪北征的史学作品,他对此事的记载很模糊: “夏六月,窦宪、耿秉自朔方出塞三千里,斩首大获,铭燕然山而还”。[31]其后范晔《后汉书》虽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但在表述上变得模棱两可——“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曰”,也露出理解上的误差,其在传后的赞论中也直呼“镂石燕然”[32]。而此后成书的《昭明文选》则直接对这篇铭文冠以“封燕然山铭”的题目,相沿成习。在唐诗宋词的吟诵之下,“燕然勒石” “燕然勒功”遂成为一种固定的认识和表达方式继续流传。
在蒙古国新发现的《封燕然山铭》摩崖对研究汉代蒙古高原地理特别是燕然山的位置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坐标信息,也提供了探究汉匈关系、草原丝绸之路、“勒功燕然”等历史文化问题的新视角。摩崖还能起到去伪存真的作用,通过对比,人们可更好地认识传世的所谓《封燕然山铭》或《燕然铭》拓片及文字来源。此外,摩崖文字也能为汉字隶书研究提供新材料。因此,《封燕然山铭》摩崖具有极高的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书法学等研究价值,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收稿日期] 2018-11-15
[作者简介] 齐木德道尔吉,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内蒙古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呼和浩特010021高建国,内蒙古大学法学博士,延安大学历史系讲师。电邮:gaojianguogood@126.com。延安716000
① 摩崖位于蒙古国中戈壁省德勒格尔杭爱苏木境内,刻在杭爱山一个支脉德勒格尔杭爱山(该山旧称Inil Hairhan)向西南突出的圆形高地之上的一座红褐色岩石上,东经 104°33′17.7″,北纬 45°10′40.4″,海拔1488 米。
参考文献:
[1] 高平,安胜蓝.历经近 2000 年班固所撰《封燕然山铭》摩崖石刻找到了 —— 专家讲述此次重大考古发现的过程及意义[N].光明日报,2017-08-16(8);朱玉麒.边塞纪功碑传统是怎样形成的[N].光明日报,2017-08-16(8);王子今.勒功燕然的文化史回顾[EB/OL].搜狐网,2017-09-18;陈君.振大汉之天声:《封燕然山铭》的历史文化阐释[J].文史知识,2017,(12);徐为民.汉匈关系与新发现的《封燕然山铭》[J].文史知识,2017,(12);辛德勇.发现燕然山铭[M].北京:中华书局,2018.
[2] 齐木德道尔吉,高建国.蒙古国《封燕然山铭》摩崖调查记[J].文史知识,2017,(12).
[3][9][32]后汉书(卷 23:窦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814.816.823.
[4]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3.2893.
[5] 通典(卷 194:边防十)[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5305.
[6] 后汉书(卷 89:南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44.
[7] 王晓毅,丁金龙.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J].山西大学学报,2004,(3):88-89.
[8] 后汉书(卷 90:乌桓鲜卑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81.
[10][11] 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 D.Erdenebaatar 等编著.巴拉嘎孙塔拉高勒茂都 2 号匈奴贵族墓葬研究(西里尔蒙古文)[M].乌兰巴托,2015.30-47.214.
[12][23] 张溥辑,白静生注. 《班兰台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90.91.
[13]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544:喀尔喀·山川)[M].四部丛刊续编史部.
[14][15][16] 汉书(卷 94 上:匈奴列传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3.3779-3780.
[17] 资治通鉴(卷 22:汉纪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6.736.
[18] 魏书(卷 103:茹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93.
[19] 内田吟风. 《魏书·蠕蠕传》笺注[C]//余大钧.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57.61.
[20] 南齐书(卷 59:芮芮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1023.
[21] 梁书(卷 54:芮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817.
[22] 魏书(卷 7:高祖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7.
[24] 崔骃.北征颂[C]//许敬宗撰,罗国威校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 347).北京:中华书局,2001.118. 《文馆词林》缺载该文标题、作者及部分内容等信息,陈君直指该文即崔骃《北征颂》(陈君.振大汉之天声:《封燕然山铭》的历史文化阐释[J].文史知识,2017,(12):10)。班固和傅毅的《北征颂》别有出处,此文又确实提到窦宪北征及“勒功燕然、饮马安侯”等语,笔者认同陈君的看法。
[25] 后汉书(卷 52:崔骃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1721-1722.
[26] 后汉书(卷 89:南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52.
[27] 张溥辑,白静生注. 《班兰台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91.
[28] 两汉纪[M].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252.
[29] 后汉书(卷 23:窦融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820.823.
[30] 崔骃.北征颂[C]//许敬宗撰,罗国威校证.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 347).北京:中华书局,2001.119.
[31] 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363.
编 者 按:原文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9 年第 1 期(总第 100 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